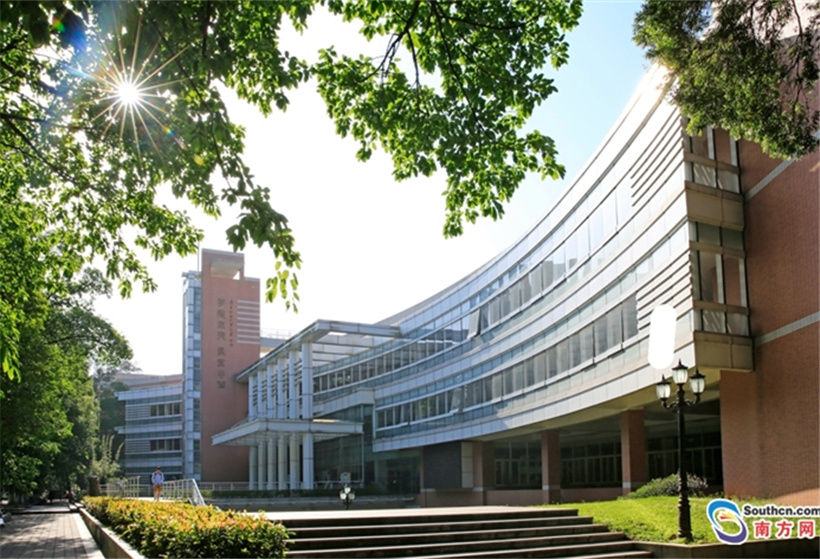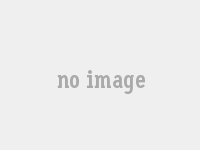■尤小立
无论是两个月前的毕业季,还是这个月的开学季,让关注大学教育的媒体最忙的似乎都是典礼上校长的演讲。姑且不论演讲的精彩与否,仅看媒体的集束报道已经够让人觉得热闹了。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校长们的演讲与娱乐新闻并列出现,双峰对峙、各领风骚,却很容易令旁观者产生一种另类娱乐的印象。
校长们的讲话当然与大众文化范畴的娱乐不同,客观地说,也是对以往缺乏人文精神的模式的一种反拨。但如果一味追求现场的效果,也未必能够走向正轨,弄不好还可能使传统不再,仪式筑于流水之上,成为把握不住的浮萍。
事实上,在典礼中讲什么、怎么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开学或毕业典礼作为一种仪式,自然是需要有属于仪式的那份庄严、肃穆,甚至刻板、程式化的一面。试想一下,一所百年大学,其开学或毕业典礼仍在遵循百年或几十年前的程序,一招一式、动静有度、一步不乱,对学生的心灵冲击肯定是刻骨铭心,甚至永生难忘的。可惜这种历史传统早已淡去,留下的似乎只有一次次的现实感过浓,甚至个人经验、个人色彩、个人表演过甚的追求。
当然,仪式是外在的,我们的教育最讲究透过现象看本质,内容总是比形式更重要。今天与20世纪初的不同,在于现今主要讲成绩,而过往则主要谈问题。1919年9月20日,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上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研究兴趣的。”与蔡元培一样,胡适也是在谈问题,只是更加直截了当。他1922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主要反省作为“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学术基础的薄弱。其中提到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别人称他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让他深感不安。胡适举例说,北大有四百多位教员,三千多名学生,《北京大学月刊》两年内却只出了五期,且常常无稿可用。“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我们自己在智识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步,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
在笔者看来,今年7月,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最能体现蔡、胡之精神。不仅是演讲中引用胡适及其两大弟子——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名言,其整个演讲所体现的风范也颇为神似。如他说:“在学术研究这一行,比的常常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不能坚持就没有收获,千万不要自我满足,别满足于SCI 、SSCI、AHCI的数量,把平庸的小土坡,当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这么掷地有声不是为了剑走偏锋、获取一时的效应,而是以一个有四十年教龄的大学教师的身份直面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直面问题,当然就是希望解决问题,使大学变得更加完善。
虽然我们觉得开学或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不见得一定要出其不意,不一定非要出语惊人,因为相对而言,朴素的话语更能留存在学生的内心之中。但我们仍然钦佩语出惊人的聪慧,也钦佩其中飞扬的文采。所有的演讲都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其中所显示出的拳拳之心和谆谆之情,也毋庸置疑。
不过,应该看到,在毕业典礼上造金句,在开学典礼上抛警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急于将长辈的经验倾诉或者传达给学生,也就是急于施以教育。但教育就其规律而言,却是慢工出细活,润物细无声,简言之,是急不得的。
而经验如果总是在抽象的或者“道理”的层面,再加之置身于度外、居高临下式的告诫,也很难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因此,蔡元培所讲的经验大多都相当具体,如他在1920年9月16日的北大开学典礼上说:“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留出多少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把课程表重新整理一番,把几种不要紧的功课、可以让学生自修的,减去了”,为此则要“预备特筹经费,扩张图书馆”。
这不是在急于教育他人,而首先是在讲自身,是对自身以及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对学生的服务进行检讨和反省,这才是一位中国大学著名校长的精神境界。难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文化保守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人们都公认蔡元培不只是重塑了北京大学,而且是真正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