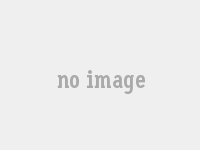2021年3月9日,合肥市瑶海区38所小学开启“三点半课后服务”,分“普惠托管”和“个性化课程”两种模式,共有名著导读、趣味编程、航模+无人机、小提琴、书法、舞蹈、长笛、武术、足球等975门课程可供学生选择。解琛摄/光明图片
1.焦虑不能停?
家长们大概从未像现在这样焦虑过孩子的教育与前程。未上幼儿园时,就要担心孩子上什么样的幼儿园;幼升小,又要担心上什么样的小学;等上了中学,又要担心上什么样的大学。上了学,还要担心上的学好不好?万一学校教育的内容不够,该怎么办?在学校教育之外,是不是该给孩子上上补习班?又要上几个补习班?总之,不等孩子到达学校教育的终点,焦虑总是不能停。只短短几代人的时间,普通家庭用于抚养孩子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的注意力和投入的金钱就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新时代育儿的基本精神几乎可以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总之,高度重视才是王道,情感上焦虑才是常态。
当然,悖论是,过去几十年间,普通人的受教育机会实际上一直在增加。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在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达51.6%,也就是说,18至22岁的成年人当中,大概有一半以上能够进入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那缘何家长总是前所未有的焦虑呢?想想二十年前,关于教育,父母要做的一般努力,大约就是“将孩子送进学校”。
学校文凭的贬值自然是焦虑的源头之一。在《文凭社会》一书中,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柯林斯曾问,现今普通人对教育投资的增加,难道就真是工作变得复杂,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不断提升的结果吗?未必是。文凭主义的泛滥不过是社会排斥需要的结果。也就是,优势社会群体需要诉诸一定的手段才能维持自身的社会地位不变,而文凭则提供了在各类职业中划分出了掌握知识的权威以及低等级的人员的可能性。
与文凭贬值交织在一起、构成焦虑的另一源头则在于不断固化的社会分层现象,家长们一要担心孩子能否保持自身的社会地位,不至于落入底层,二要探索孩子持续的社会流动、实现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对于普通城市家庭,这两重考虑可能尤其如此。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埃伦瑞奇在分析该国中产阶层的世界观转向时,曾提及他们“担心失败”(the fear of falling)的心态,并将其视作理解当代中产背景家庭重视教育并不断增加教育投资的观念根源。埃伦瑞奇认为中产的立身之本在于他们自身的专业化工作。但专业知识本身又不同于拥有金钱和资产。后两者是上层人士较为有效的社会排斥手段——难以为其他社会群体的人轻易获得,这就意味着在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设置了一道有效的藩篱。但中产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本身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对于中产和他们的子女而言,专业知识堆砌起来的壁垒并不坚固,除了投资教育,不断给孩子压力,让他们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以外,似乎别无他途。
2.贩卖“焦虑”——商业机构销售教育的核心技巧
我要强调的是,在当代社会,家长焦虑的另一源头是商业机构——既包括教育公司、商业化的教育机构,也包括商业传媒。它们不断渗透进学校教育系统,贩卖“焦虑”是他们核心的销售技巧。
所谓贩卖焦虑,核心是制造“欠缺感”,兜售需求。欠缺感,就是一种“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感觉。例如,通常育儿机构营造的意象就是你还缺乏足够的育儿常识,或者说和别人比较起来,你的知识还不够,而这一点可能导致“你的子女输在起跑线”,那么就把孩子交给“专业人员”,要不就买几本“育儿常识”“学习学习”。近年兴起的“家长教育培训课程”,其销售前提也是告诉你:教育孩子,仅凭一份热情还不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巧,便无法成为“有效的家长”。商业机构制造欠缺感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告诉你,“别人都在做,而你却不在做”。看到无孔不入的商业广告上,别人家的孩子都手拿学习机、结合当今最流行的教育技术学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心虚呢?看到报道上,补习机构里满眼都是孩子在补习功课的时候,你还能不如坐针毡吗?当受众最广的传播平台都在一遍遍刷屏校外线上培训机构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然觉得这个世界只剩自己的孩子没有上培训班了?最让人揪心的商业运作,则是告诉你,在面对教育时,不同的社会阶层面临不同的选择。来自底层的孩子在放弃,来自中层的孩子在应试,而来自上层的孩子在享受教育,而你则要选择哪一种道路?
贩卖焦虑的第二方面是销售所谓“正确”的教育方式。商业公司本身往往会迎合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教育理念,声称教育方式有着多样化的选择。问题是“多样性”本身往往难以捉摸,普通家庭的教育实践也往往难以透过大型媒体广泛传播。商业公司则往往占有独特的优势,借助自身的话语权——对影响力稍大的媒体的占有——定义何为“专业”与“合理”,“科学”与“正确”。被包装上市的“虎妈”和“狼爸”的育儿故事,尽管本身揭示了家庭教育的多样性,却无一例外地被媒体展示为:有一条可被学习和复制的家庭教育范式。成功者故事的兜售,是商业利益使然,所谓“正确”,则是故事销售的保障。你是否会“正面管教”?又是否掌握了“培养孩子专注力的60种方法”?在全民鸡娃战中,你如何做到“务实”?“慢慢来”是不是更加“正确的姿势”?网络神曲“我们不一样”大概是对差异的有感而发。但在育儿这件事情上,父母不能容忍“我们不一样”,不一样的只能是资源(那在父母的控制之外),观念上绝不能犯错。因为孩子的生活是由他们能得到的养育质量决定的。无处不在的商业营销好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怎么养育孩子将对他/她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贩卖焦虑的第三方面则是鼓吹竞争的意象。当代研究人员针对社会分层与教育间关系的研究,最起劲的鼓手,应该是商业性的以售卖教育产品为己任的公司。目前,研究人员能够证明教育或能影响个人流动的机会,但决定一个人生命际遇的,的确并不完全在教育。然而,在商业公司那里,教育却成为维系着一个人一生幸福与际遇的唯一,是个人获得竞争力的基础。而当代社会全部的社会关系,可以全部地抽象化为竞争二字。父母的教育使命,则在于培养出适应社会竞争的孩子。所有教育的行为,不过在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教会孩子领先其他孩子的技能。在我们这个年代,“高强度育儿”已是主导的育儿模式。在高强度育儿的话语体系之下,父母的幸福和子女的一切取决于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和竞争意向一起被鼓吹的是“父母决定论”——孩子发展的好与不好和父母是否职称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对父母养育行为也有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快,要力争做全能父母,要为孩子创造美好的童年,因为他们需要为一个竞争的年代做好充足的准备。
3.“焦虑”缘何得以维持?
资本对教育系统的强力渗透,一方面缘于近代教育治理理念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市场被看作是更加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手段,放松管制、教育供给的公私合作都成为可能,自然也为资本进入教育系统打开一扇窗。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商业公司自身强大的影响力。
但商业公司所兜售的“焦虑”是否能够扩散并持久地保持下来则被如下几个因素影响。第一是焦虑情绪本身是否迎合了人的本性,第二是它是否能够与当下独特的社会生态、经济条件挂钩,第三是这种情绪本身是否能够借助技术得以广泛传播。不幸的是,担心匮乏,因为“欠缺”而产生焦虑正是人性的基本特征。而当下持续的社会转型与地位分层则提供给了商业公司编织教育与个体竞争力之间决定性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则增加了家庭投资的“风险意识”,是否能够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或者成功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败似乎在“教育”一举。媒体的扁平化使得群体性的情绪更易获得传播,加上群居本性,稍不留神,个体就能变成群居性感受的接收者,成为“焦虑”这一特定社会心态的建构者、参与人。
孩子从来都在父母手里,但教育未必。父母为子女所构建的伟大教育工程,说不定正在资本的手中!(作者:谢爱磊,系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