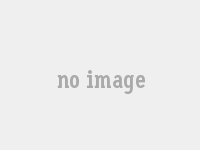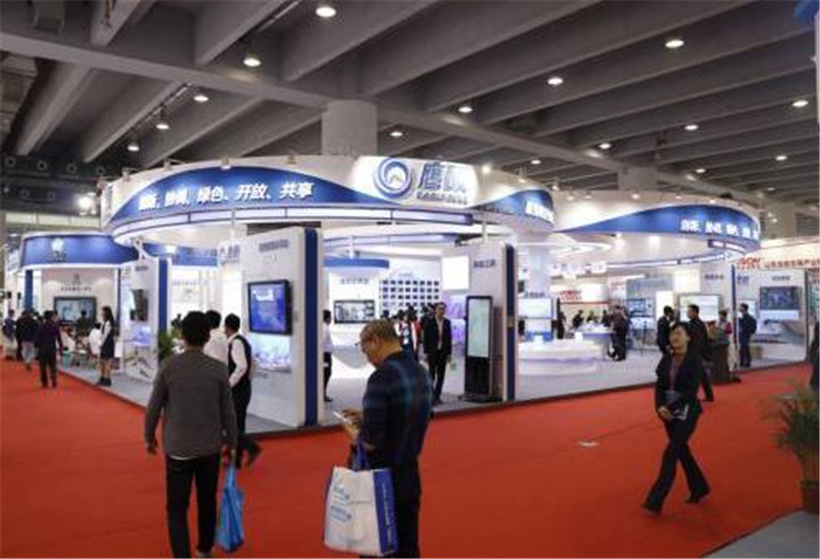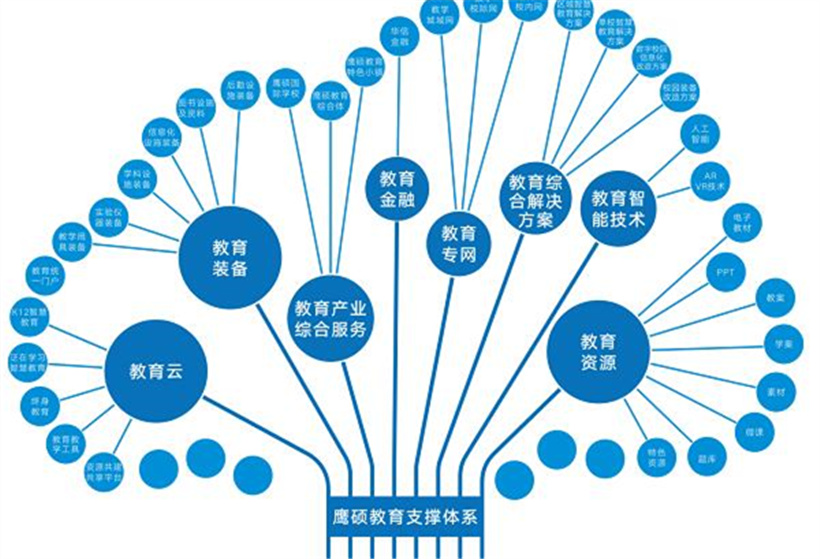12月5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新民空间,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教师徐莉老师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老师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谈,针对中国内地、香港、丹麦三地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并与参与沙龙的观众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如何在异质的经验中寻找另一些教育创新可能。
徐莉:丹麦、内地、香港,三种不同的教育生态
我曾在丹麦生活过一段时间,前不久又参加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的教师培训。这次重返,我特别希望可以知道丹麦人对于教育的理解。
我这次的分享没有答案,全部都是问题,我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全人教育?把所有我们认为好的知识都教给学生,一样都不少,就是全人教育吗?
内地:“代币制”的鼓励方式我在很多场合中听到教师、家长表达的一个困惑:到底应该怎样鼓励孩子?在内地,有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给小红花、评三好学生,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代币制”的教育。在这种“代币制”之中,孩子的感受到的压力不是孤立的,我们的老师、家长也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各种大奖、各种评比在等着我们,好像无时无刻在比谁的小红花更多,在这种教育中,个人的意义感和价值感是缺失的,职业发展、学习本身的乐趣也被磨灭了。结果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别人认为正确、重要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学习的自主权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整个教育体系中,其实不管是孩子和老师,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限制和制定规则。这次去丹麦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相信,不批评、不给奖赏孩子们也可以成长得很好。
丹麦:自在的教育我想通过几个问题来分享,丹麦的教育。
首先是,我们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希望孩子明白是什么是上课、什么是下课?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张丹麦某个幼儿园的一日时间表,你会发现,他们自由度很高,有集中学习的时间,但是时间很短,也不是总在学习新知识,没有强迫式的学习,有大量交往的时间和讨论的时间。另外,在幼儿园做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有漫长的开始和漫长的结束,老师会发出明确的信号,然后相信孩子可以把事情做好。
第二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可以为自己做出选择?
从这个幼儿园的午餐时,我们注意到低龄幼儿坐在就餐椅上,有老师在喂食,但是孩子自己可以随意抓取食物,弄得满身都是,但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不卫生的。我认为,孩子为自己做出选择是从伸出手抓的动作开始,甚至从哭着想要换尿布开始。
第三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可以离开大人的视线。
丹麦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区域,有很多玩乐设施,我们注意到这里还设计了很多躲藏的地方,因为孩子有时候不想被被人看到。大人们相信孩子会保护自己,会在交往的过程中慢慢设定自己的界限。
第四个问题,孩子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历史?
孩子在博物馆里面用历史的东西去玩游戏,他可以穿过去的衣服,坐在过去用的船上,只有移民入籍才需要纸笔考试丹麦历史。
丹麦人的核心价值观——Hygge,代表一种很享乐、舒服的状态。丹麦的孩子成长得很自在,自在在于从你一出生就有人在乎你,幼儿园的窗口设计得高低错落有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高度的孩子去观察外面;自在在于其“刻意性”,幼儿园的地图都贴在地面或者靠近地板,方便孩子去寻找位置;自在来自对孩子的尊重和信任,幼儿园的玩具都使用质量很高的经典设计,比如不用认识五线谱也可以玩的打击乐器,不让学习成为一种障碍;自在来源于目标设定,在上自由戏剧(即兴戏剧)的时,老师会花大量的时间询问孩子的心情、兴趣,孩子的自我表达会推动戏剧的产生,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低龄孩子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在丹麦,你会有这样学习的体验——原来学习的过程没有指责和羞辱是可以实现的。
丹麦人对“玩”的教育学理解
在丹麦,低控制的教育并不意味着放任,所有的学习环境都有让孩子观察、体验、缓慢进去的机会。假设画一个坐标轴,极端放纵在左边,极端控制在右边,那丹麦的教育在哪边呢?我问过当地的教育者,他们认为丹麦的教育在中间。他们的自由不是放纵,其实他们对孩子是由期待的,成长的过程一直在不断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只是达成这个的手段不是奖惩,而是营造这种环境。
香港:“学习压力”的不同表现香港的办学比较自由,政府允许大家申请办学,但是有详细的标准,细化到学校建筑的图纸,政府补贴到学校的每一分钱都会被监督。家长可以在居住的学区内自由选择学校,而学校招生不够的话,老师和校长就会失业,这样学校实际上也面对着很大的压力。这样的状况下,教育管理部门不是官员,只是一个提供支持的机构,并不干预学校的办学。
在香港,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即使是普通中学,你可以看到,孩子们早上到了学校是不可以自己先进教室的,而是在外面排队,由老师带队进去,在学校上下楼梯这件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进行。进了教室之后,基本就没有再出来的机会了,他们一般没有课间十分钟,也就是课都是连堂的,午饭之后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休息,可以由班主任带到一楼休息,然后上楼继续下午的学习。他们三点半就放学了,因为这个时候家长多半都在上班,所有孩子们又进了培训班。他们的作业通常由三部分组成,教科书+辅导书+老师设计的作业(称为“工作纸”)这意味着不仅学生的压力大,老师的工作量也会很大。
在香港的国际学校可能不会这么夸张,但普通学校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香港普通家长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孩子的社会公民和规范基本都由学校来培养,所以学校老师会很严格。香港孩子们的勤奋、严格的纪律规范都让我既佩服又感触良多。因为整个社会有很强烈的的隐忍、坚韧、勤奋的氛围。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香港有一个考试叫全港性系统评估(简称TSA),是全港的学业水平测试,分别只考三年级和六年级。但是香港大众认为这导致了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于是他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取消了三年级的TSA。而教育局认为,一个不公开成绩,并且不会对学校、学生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的评估,本意只是用来改善教学,被大众这样毫无专业考虑地取消掉,不利于提高教育的水平,于是只好换另外一份评估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在反对声音当中提高自己自我阐释的能力和理解对方的能力。
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也回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教育中没有指责和奖赏就是放纵吗?不,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自由;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你是不敢为之,还是你并不真的相信?教育的问题常常在教育之外;我们的教育出发点真的是为了儿童的一切吗?不,我们的教育理念其实经不起推敲,我们头脑中先在的比儿童更重要。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格隆维那样的推动者,从各个视角推动对教育政策。
现场听众对徐莉老师的分享很感兴趣
对谈:学校的作用是通过教育解决人的问题
之后,徐莉老师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就三地的教育生态展开了深入的对谈。
杨东平:现在中国也在提倡低竞争、低管控、低管控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保证儿童睡眠的教育,这看起来很困难,但是仔细想想这不是儿童最基本的人权吗?在丹麦,九年级以下的学生甚至没有考试,虽然会有一些练习,但成绩单上没有分数,更没有排名,练习的目的是对老师教学的反馈,让老师能够调整教学。 丹麦前段时间还通过法案,重申play is king,就像那句经典的话,“孩子不会为了学习去玩耍,然而学习会在玩耍中自然产生”。他们的幼儿园也会允许儿童不高兴、沮丧,这都体现了对儿童的尊重。
丹麦的高中毕业生里面相当多的人选择不去上大学,这与非常灵活的学校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的学生从7年级开始就可以选课了,分成科学、艺术、商业三个方向,学生可以同时选两个,实习两个星期再确定一个方向,这样的制度给了学生很大的自主性。学生还可以选择读10年级。10年级为有选择困扰的学生提供的一个过渡期,帮助他们自我调整,寻找自己的兴趣方向。由此,反思中国应试教育的改善,其改革关键在于高中教育的多样化,让更多人在高中就能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
徐莉:丹麦的教育提供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当你选择了之后发现自己不适合或者对其他更有兴趣,就可以转变。分流不可怕,可怕的是分流之后人生被确定了,没有选择的人生很恐怖。
杨东平:丹麦还有一种很独特的学校——民众学院,是19世纪格隆维为农民创办的“生活学校”(关于生活学校的信息可点击这里)。我们可以思考,在现代教育已经普及的情况下,民众学院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是它为成年人提供了短期教育,更重要的是,它是成年人的精神避难所,为成年人提供了自我调整的机会,让他们可以重新出发。在台湾,社区大学也有这样的作用,它为成人提供了交往的空间。因此,民众学院和社区大学都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
徐莉:杨老师刚刚提到的格隆维很重要,丹麦是个民主国家,民主意味着你有这些权利,需要参与,但是你没有能力,你不识字,所以就需要这种学习机会来帮助你兑现。学校是为了聚在一起,通过教育解决人的问题,不是为了传授或者传递,而是为了帮助人。
问答环节
Q1:丹麦教育有没有弊端,弊端是怎样的?
徐莉:我认为无所事事并不是真正的对儿童的理解,儿童的确有自己慢慢去寻找、探索的天性;但是儿童还有一个特点是对权威的尊重,这在丹麦的教育中都有体现。
杨东平: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在国内减负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快乐教育是欺骗劳动人民的幌子。其实,在玩中学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例如,在美国,真正竞争性的学习是从高中才开始,他们认为人就应该被尊重、被宽容;在丹麦,初中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度过青春期。中国的教育则是选人出来,这里面有一种控制机制、选举机制,但是丹麦不一样,大家觉得孩子在某个时代合适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或许与人口数量有关,北欧文化中认为每个人都很珍贵。他们小学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保持孩子的学习热情。
Q2:香港的孩子是什么感受?难过?幸福,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成人怎样看待自己受的教育
徐莉:香港孩子只是不做声,表现出克制,其实他们的学业成就感和幸福感非常低。他们最开心的就是一天中被老师领下楼的20分钟,幸福感很低,学生表现出克制。但是到了中学会好很多,因为增加了很多有趣的课程。香港的大人认为教师是很好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收入是和医生一样的,他们的幸福感来自于对这个职业的认同。
Q3:名师在上课的时候,会有班级币,回答问题多就会给,相当于一个奖励,我自己的授课中也有冰冻椅子、安静角,其实都是没有说出来的惩罚。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那怎样去调动我的课堂?怎样管理孩子呢?
徐莉:小红花有其积极的意义,能够带给孩子成就感;但同时又破坏了孩子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当我和孩子一起去做他们喜欢的课时,我不需要用到小红花;二是当我发现孩子不愿意上某些课的时候,我会考虑有没有其他内容可以替代,所以也不存在用不用小红花的问题;三是去反省那些看起来短期很有用的东西,它们其实可能是有害的。
彩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老师也来到了现场,谈了他的感受。
康健:我问过一个孩子,什么是时间?孩子说时间就是铃声+吼声。我们知道松弛的校园成本是很高的,自由的代价很大,但人只有在自由、松弛的状态下才是真实的。
我始终认为教育质量的问题是教育公平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目前推动教育公平很多都是给学校增加设施设备,这只是“标配的公平”,例如我们的学校里有一个班,里面至少有1/4是残疾、单亲、或者家庭环境很复杂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标配的公平并不公平。另外还有很多乡村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师资水平特别有落后,做教育需要了解农村孩子真实的状态。这个问题的提出就代表了我们教育的功利性,我们的校园是没有温度的,赤裸裸的。
杨东平:就是公平的问题。另外也有很多人在问北欧国家这种高福利,低控制的教育不就是培养懒人吗?其实不是,北欧人的创造能力在全世界来比都是很高的,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创造力。